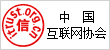|
据《论语·子罕》,有一天,子贡问孔夫子:“有一块美玉在这里,是放进匣子里藏起来呢?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买主卖掉它呢?”孔子说:“卖掉它罢,卖掉它罢,我等着买主呢!”这段对话形象表明,儒家知识分子用世之心不仅可谓与生俱来,而且近乎迫不及待。 既然讲究用世,必得把自己推销出去,而在君主政体下,皇帝就是最大的买主。至迟在南宋,话本里已有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的谚语。稍有点儿“文武艺”的待价而沽者,无不指望在皇帝那儿卖上个好价钱。就儒臣而言,能当上帝王师,给今上传道解惑,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。 宋代给皇帝讲课的官员称为经筵官,具体有翰林侍读、翰林侍讲、崇政殿说书等名衔。皇帝开经筵,用意无非“听政之暇”,“以备顾问”,有时也会特召宰相、副宰相们前来听讲。每一书讲毕,都会有所赏赐,往往还说上一句“诚哉斯言”的褒奖语。尽管宋代皇帝文化素养较其他朝代为高,与经筵制不无关系,但经筵制毕竟寄生在君主专制的母体上,绝不能盲目高估。 在两宋名臣中,史学家司马光、范祖禹与理学家程颐与朱熹都做过经筵官,给皇帝上过课。但正如刘子健在《中国转向内在》里指出:“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,其心态和行为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,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”。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,宋代未能消解王朝周期律的魔咒,其政治生态也随时代推移日趋恶化。与司马光等北宋经筵官相比,南宋朱熹的帝师路也许更耐人寻味。 二、 南宋前四帝倒有三朝没搞终身制,但并非尧舜禹禅让那样无关血缘关系的选贤与能;只不过皇位在父皇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已。尽管如此,却还安上一个美名,叫做“内禅”,也就是皇室内部交班。第三次禅代在紹熙五年(1194)七月,故史称“紹熙内禅”。其真相是第三代皇帝宋光宗以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将近三年,大内宫女都背地叫他“疯皇”,朝局实在无法支绌下去,这才在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手推动下,对外美其名曰禅让,实际上是废旧立新。第四代皇帝宋宁宗智能庸弱,从总体上说,作为君主绝对不合格与不胜任;但他是惟一的“皇二代”,这“禅让”出来的皇位还非得由他来继统。紹熙内禅凸显了君主世袭制的全部荒谬绝伦,朱熹就在这一背景下踏上了帝师路。 禅代次月,一方面出于赵汝愚力荐,另一方面内朝也早闻其名,宋宁宗召朱熹为侍讲。在任命告词里,皇帝首先强调对经筳的重视:“朕初承大统,未暇他图,首辟经帏,详延学士。”接着道明了期待:“若程颐之在元祐,若尹焞之于绍兴。副吾尊德乐义之诚,究尔正心诚意之说。” 希望像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,尹焞主讲宋高宗的经筵那样,为报答我尊德崇义的热忱,来发挥你正心诚意的学说。 宋宁宗不但钦点了朱熹为首的十名经筵官,还亲定了十本经筵讲书,宣布即日开讲,隔日一次,经筵官轮日赴讲,早讲于殿上,晚讲于讲堂,其力度之大,频率之高,在两宋也算得上空前绝后。或即如此,士大夫将新君即位首开经筵誉为“新政第一”。 朱熹收到告词不久,朝中友朋也驰函来告,提到“主上虚心好学,增置讲员,广立程课,深有愿治之意”,还说皇帝一再问到他。朱熹有点受宠若惊,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里说:“果如此,实国家万万无疆之福,义不可不一往”。专制政体下的知识分子,太容易被新君新政所感动,而不吝赞辞,引颈企盼,连朱熹都不能免俗。 入朝之前,有学生问老师:“皇帝虚心以待,敢问其道何先?”朱熹明确指出:“今日之事,非大更改,不足以悦天意,服人心。”大更改,意即大改革。他尽管不无乐观地相信:“天下无不可为之时,人主无不可进之善。”却也明白,这种“大更改”,“其事大,其体重”,前行之路布满荆棘。朱熹以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决心,自明心迹道:“吾知竭吾诚,尽吾力耳,外此非吾所能预计也。” 进入南宋,中国全面转向,按刘子健的说法,“权力逐渐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,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,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。”高宗朝名儒胡安国,“以圣人为标的,志于康济时艰”,“每有君命,即置家事不顾”。宋高宗表面上礼贤下士道:“渴欲相见”,请他做经筵官,但据《宋史》本传,安国从考取功名直到去世,“四十年在官,实历不及六载”,大部分年份都被皇帝与权相以一介闲职晾在一边。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,“一些知识分子还是会去当官。他们又能说些什么?尽管无法明言,但他们明白,这是一个时常会堕落成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。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。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,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。这就是伟大的新儒家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,齐家在于修身,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的奥妙。”(上引刘子健书)朱熹正是抱着“给皇帝注入新动力”的心态,决意入朝去做经筵官的,这也是他生平惟一一次入朝供职。 三、 六和塔下的浙江亭是南线进入临安的最后一个官驿。九月末,朱熹在这里受到了盛大欢迎,迎迓者中既有叶适、陈傅良与薛叔似等永嘉诸贤,还有刘光祖、彭龟年、黄度、章颖等在朝名士。借用余英时的说法,参与六和塔之会的衮衮诸公,“在朱熹征衫未卸之际便赶紧和他进行关于改革步骤的热烈讨论”。毫无疑问,这些人以宰相赵汝愚为旗帜,与朱熹同样主张“大更改”。 十月二日,朱熹入临安。四日便殿召对,他终于得见天颜,连上了几道劄子。第一札要求新君正心诚意,第二札专论帝王之学,希望皇帝孜孜不倦,自强不息,“以著明人主讲学之效,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”,期望值够高的。宋宁宗也再次强调:“你经术渊深,正资劝讲,以副我崇儒重道之意。”不久还给朱熹以赐食的殊荣。 朱熹自我感觉良好,以为这下可以得君行道了,迫不及待地“致君尧舜上”。十四日,为皇帝开讲《大学》。在进讲日程上,宋宁宗已经加码:每遇单日早晚两次进讲,只有双日及朔望(初一、十五日)、旬休、假日停讲,大寒、大暑也是罢讲月份。朱熹进一步建议:今后除朔望、旬休与过宫探望太上皇的日子,不论单双日都早晚进讲,只有朝殿的日子才暂停早讲一次。皇帝表示同意,首讲结束时还降旨表彰:“来侍迩英之游,讲明大学之道。庶几于治,深慰予怀。” 其后进讲,朱熹首先把讲课内容编次成帙,然后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,还不失时机地对应君德与时政。一次进讲后,他问皇帝:“不知所进《大学讲义》,圣意以为如何?”宁宗若有所悟道:“看来紧要处,只在求放心啊!”高兴得朱熹连忙顿首称谢:“陛下拈出这‘求放心’之语,正是圣学要领,愿推而广之,见诸实行,不愁不为尧舜之君!”归来后,他喜不自禁对门人说:“皇帝可与为善,但愿常得到贤者辅导,天下有望啊!” 在朱熹看来,新君中人之质,可与为善,也可与为恶,关键在于变化气质。他更意识到作为帝王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。 新君一意向学的热情与礼敬讲官的谦逊,让朝中士大夫大受鼓舞,说他“即位之初,首下明诏,博延儒英,增置讲读,细绎经史,从容赐坐,一日再御,情无厌倦”。皇帝也对经筵官们提高了要求:“今后晚讲,各须讲解义理,引古证今,庶几不为文具。”宋宁宗不可谓不好学,然而,圣主明君固然不能不读书,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。 四、 宋宁宗初政,以赵愚汝为政治领袖,以朱熹为精神领袖,时论认为“从赵公者皆一时之杰”,于是,“众贤盈庭,人称为小元祐”,似乎有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。但新君初政的所作所为主要出于赵汝愚的影响;其本人在知人理政上可以说比发精神病前的宋光宗还成问题。 禅代次月,赵汝愚拜相,他“尤重惜名器,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”。韩侂胄自以为有拥立之功,对节度使垂涎三尺,也遭到裁抑。韩侂胄充满怨望,决意对赵汝愚发难。为博取皇帝的好感与支持,他利用知閤门事得以传递内批的职务之便,鼓动新君以御笔独断朝政。朱熹察觉到这一动向,在一次经筵讲毕后上疏皇帝,对其独断发表谏言: 陛下独断,即便其事悉当于理,亦非为治之体,以启将来之弊。况中外传闻,无不疑惑,皆谓左右或窃其柄,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?此弊不革,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,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。 宋宁宗全然不反省自个儿为政之非,只向朝臣转发了这一奏疏。 韩侂胄见奏疏只差点出自己的名,勃然大怒,深感朱熹的威胁比赵汝愚更切近直接。一来,朱熹是理学领袖,具有登高一呼,应者云集的号召力。二来,朱熹任职经筳,能经常不断地施加影响,说不定有朝一日皇帝真听从了他的进谏,来个“远佞人”,将自己给黜逐了。他决定率先将朱熹排击出朝。 在经筵上,朱熹“急于致君,知无不言,言无不切,颇见严惮”,早让皇帝如坐针毡。这天,优伶王喜受韩侂胄唆使,刻了一具木偶像,峨冠大袖,在御前献演傀儡戏,仿效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,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,既丑化朱熹,又试探皇帝。宋宁宗看了,不但不制止,反而加深了对道学的厌恶。韩侂胄见投石问路倾向已明,便趁机进馋道:“朱熹迂阔不可用!”对朱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,论上一番,宋宁宗内心很不耐烦。他对另一经筵官说:“始除朱熹经筵而已,今乃事事欲与闻。”透露出这种不耐烦压抑已久。 闰十月二十日,经筵晚讲,朱熹抓住正君德、行治道的机会,借发挥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正心诚意”大义,当面批评新君“但崇空言,以应故事”。宋宁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,晚讲一结束,就给朱熹颁下御笔: “朕悯卿耆艾,方此隆冬,恐难立讲,已除卿宫观,可知悉。” 话说得冠冕堂皇,顾惜年迈啦,考虑天寒啦,实质上给一个不须赴任的宫观闲差,打发他回家。 宰相赵汝愚得知消息,还想让皇帝收回成命,甚至不惜自求罢相以为谏请:“必欲逐朱熹,汝愚退而求去。”宋宁宗怒气愈盛,认定他为助朱熹竟然不行人主之令。其他官员也反复谏止,宋宁宗扔下一句:“朱熹所言,多不可用。”对朱熹讲课给出了最终评分。惟恐夜长梦多,次日,韩侂胄命内侍缄封了御笔面交朱熹,这种罢免方式在宋朝是违背制度的。朱熹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彻底转向,他算了一下,入朝为经筵官只有46天,先后给皇帝仅上了七次课。 五、 朱熹只能凄惶地辞别临安。行前,史馆同僚到他寄寓的灵芝寺饯行,知名的有叶适与李壁,后者是著名史家李焘之子。席上,朱熹黯然神伤,吟诵起南朝沈约的诗: 平生少年日,分手易前期。及此同衰暮,非复别离时。 勿言一樽酒,明日难重持。梦中不识路,何以慰相思。 是啊,年轻时分别是为换取将来的期待,现在都到了晚年,不再有过去别离的那种情怀。别说这一杯苦酒,不知明天还能否与诸位共同举起。梦中已认不得路途,拿什么来慰籍思念之苦呢? 这不识之路,当然不是指归乡之路,这难慰的相思,也不仅仅指对知己的忆念,都有着更深沉远大的寄托。其中应有朱熹梦寐以求的“得君行道”之路,也有他毕生追逐的“内圣外王”之梦。这种近乎失态的难以自持,在朱熹一生中也是少见的。李壁表示,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,请他挥毫书赠以为纪念。朱熹苦涩道:“像我才知道其味,你还没有,怎么也喜欢这诗呢?”李壁时为35岁的年龄与阅历,不知是否真能咀嚼出对方内心的滋味。但朱熹后来还是手书相赠,借古人的诗句向自己昔日的外王梦与帝师梦作最后诀别。 大约一两天后,朱熹在俗称北关的余杭门外上船南归,也还有人前来送行,但朝局逆转,士林失望,已非复六和塔之会。他在给刘光祖信中怅然感慨:“北关之集,风流云散。甚可叹也!” 尽管沮丧失望,朱熹其时却未必逆料:接踵而来的庆元党禁竟全面动用专制权力,把以他为代表的理学一巴掌打为“伪学”,对理学家们实行了全面的整肃与空前的迫害,他也在酷烈的党禁中离开了人世。 六、 有人也许异议:朱熹当帝王师恰赶上韩侂胄借反道学打击政敌的当口,实属时运不济;倘若在崇尚理学的君主那里,就不会落到最终走人的结局。 南宋第五代皇帝是被正史推为“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”的理宗,尽管在公开場合表彰理学,从周敦颐到朱熹等理学大师也被他请进孔庙供奉起来,他也做秀听过好几次新儒学讲座,来为又一次“更化”做秀。但后世史家一针见血道:“他所关心的大多是些非儒家的放纵”。这有《宋史·理宗纪》为证:“嗜欲既多,怠于朝政”,“经筵性命之讲,徒资虚谈,固无益也”。 还是刘子健说得好,那些专制政体下入朝做官的士大夫,“偶而,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,但其努力鲜能奏效,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: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,要么走人。”据此推论,即便在理学业已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宗朝,即便朱熹再世而入讲经筵,在同流合污与出局走人之间,他也只能二者必居其一。当年给宋理宗上课的经筵官,都是货真价实的朱熹传人,虽不能断言他们都像时人抨击的那样:“外示雍容,内实急于进取,口谈道义,心实巧于逢迎。”但在政治生态日趋恶化的情势下,曾经起过点作用的经筵讲课,也只能沦为君主独裁的装饰,舆论监控的屏风。 (责任编辑:PAUL ZENG) |






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。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、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、侨海网有限公司。
为侨海网专有标识。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、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、侨海网有限公司。